在进行这些描述时,我已经回到了南方,继续写着市委书记的材料,这在一些矢志仕途的人看来是一项很神秘很重要的工作,但是我心不在焉,总是热衷于参加一些文学的活动。同时,我开始听到一种说法,一种在南方民间比较骇人的说法,说是在父母去世的那一年,是一个很倒霉的年份,做什么事都不成,还会遇上其他霉运。父亲在2006年12月29日去世,2007年元旦做法事,喃斋,很不巧就是新年的第一天,这被我当地的一些很信命运风水的朋友看成是诸事不顺的兆头。我的老上级陈启就把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:“那年,我的父亲亦系得了绝症,放上手术台后就落冇来了,结果整整一年,诸事不顺。我做了六年副镇长,好冇容易盼到了升副书记的机会,眼看考核在即,冇知何故又停止了。死老豆(父亲),系衰到底啯,估计你亦好冇到哪里去。”
1月2日,我父亲下葬,又逢上我的阳历生日。这些奇怪的巧合我当时没有意识到,那时我正处在悲伤之中。
临近暑假的一天下午,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写讲话稿,突然接到依力幼儿园吴老师打来的电话:“你女儿呕吐了,还发烧,你快来接她去看医生吧!”我大惊失色,我们夫妻三十好几才得女,女儿是心尖儿肉,稍有个头疼脑热我们就高度紧张。我马上放下手头的稿子,一边走一边想,怎么会呕吐呢?可能就是一个感冒吧。但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电话给阿依,她在医院上班,我让她赶紧预约好医生。
见到了依力蜡黄憔悴的脸蛋,我抱起她,心头一阵收缩,她软塌塌地倒在我的怀里,平时浓长活泼的两道眉毛像两条病蚕耷拉着,本来很好看的长睫毛像两把枯草,遮掩着她那双大眼睛。我问她哪里不舒服,她低声说头痛。
“她刚刚呕过,”年轻的女教师怯怯地对我说,“她呕了一摊,我就赶紧给您打了电话。”
我把依力抱出幼儿园,发动了摩托车,是那种女式摩托,我把依力放在前面踏板上让她站着,再用双腿紧紧地夹住她,她半躺着靠紧我,一脸疲惫的样子,我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。
满脸紧张的阿依正在儿科门口等着,带我们去找医生,测体温发烧39.5度,医生认为是感冒,开了一点退烧药,回家后我给依力服下,但没有见效,她还是发烧,还是说头痛,还是伴随呕吐。我们赶紧又去找了另外的医生,吃了他开的药,依然不见好转。那晚依力折腾了一夜,我们也熬了一夜。
“只能去找廖主任了,她是儿科的权威。”阿依说。
我对找谁看病毫无主见,心里只剩下惶恐和对阿依的希望。天亮我就盼望快些到上班时间。我们提前半个钟头去医院儿科门口等候,像等候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人。
儿科廖主任是一位精瘦的女士,她花了半个钟头为依力做常规检查,做了详细询问,确诊她患有上颌窦炎,得知前段时间她老出鼻涕,我们给她吃了太多的西药,就说:“可能把胃吃伤了,她还有药物过敏性胃炎,我还担心上颌窦炎引起脑部问题,怀疑她脑部感染,你们要让她住院观察,要检查血液,拍X光片。”
我看到阿依本来暗黄的脸刹那间就变成了白纸般的颜色,我还看见了阿依惶恐地看着我的眼光,那里有我苍白的影子。我机械地听着廖主任的意见,头重脚轻地出门去了收费处,办了住院手续,又脚步轻飘飘地回来。廖主任命令护士试针,护士拿起了小针管,依力惊恐地瞪着针管,哭喊:“不要打针,不要打针!”阿依抱着依力,我扳着依力的手臂,护士给她小手腕涂了棉签消毒,针管就扎了进去。试针无事,开始抽血,要抽静脉血,还要抽动脉血。护士拿起了比拇指还要大的针管,针管前端那又粗又长的针刺明晃晃地伸过来了,我再次扳着依力的手臂,她已经被吓得不敢动了。粗长的针刺像刺刀一样扎进了瘦小的手腕,我似乎听到了“啵”的一声穿破皮肤的声音。暗红色的液体像泉涌,在拇指大的针管里涨起来。依力哭,喊“疼,疼”,泪水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一滴一滴从她脸上滚落。大头针管里的暗红越来越满了,它来自两岁多的瘦小的依力的身体。阿依眼里噙着泪,抱着依力不敢动,嘴里只说:“依力不哭,依力不哭,马上好了,马上好了……”两次十几秒的抽血,我的心仿佛被放进了油锅里,煎熬。依力...
依力住院后,我们就以病房为家了,我顾不上市委书记的材料有多重要,有多紧迫了,我想,如果依力有三长两短,我要这份重要的工作又有何意义?我木然地待在病房里,忧愁像惨白的墙壁沉闷地包围着我,又像吊针里的药液,一滴一滴地注入我的心脏。阿依神经质地频频看着输液瓶,滴得慢了就摁呼叫铃,护士一次次过来,轮到换第二瓶药液的时候,大概已经来过五六趟了。我满脑子都是女儿憔悴的脸蛋,都是她蜡黄的面容。我只跟领导说了一声,就日夜待在医院,守着依力不肯出来。阿依那时已经是医院的办公室人员,一个萝卜一个坑,但身为外科医生的院长很理解她,愿意放她的假,专门抽了一位人员暂代她,她对自己撂下工作心怀惭愧。那些日夜,我和她在病房守着,凝视着依力,目光一刻也不敢离开,有什么不适表现总是急急忙忙找医生。
抽血化验之后,几个医生开了一个会议,一个医生要阿依去办公室,几分钟后,阿依一脸戚戚地回来,悄没声息地坐在床头,不看我,看着依力,说:
“他们说要做腰穿。”
“腰穿?”我没反应过来,但看阿依的表情,知道事情不好。
“就是抽取脑脊液作进一步检查。具体结果,要等脑脊液检查之后才敢肯定。”
抽了血之后还检查不出病症,证明问题很严重了。我的心顷刻就坠了一块巨石。谁能体会到我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啊!头晕目眩,两眼发黑,两腿发软,双手也无力,就像灵魂早已被谁吸走了。
阿依让我守着,自己一个人轻飘飘地去了医生办公室,几分钟后她心事重重地回来。
“科里打算让一个普通医生做,说是这个手术很简单,”她满脸愁容地望着我,“我想找人跟廖主任说一下,让她亲自做。”
她和我在依力的床头相对坐着,既惶恐又焦虑。我明白了,由一个普通医生来做,她实在不放心。我受不了啦,掏出手机就找我单位的同事,让他帮忙查到了院长的电话,我拨通了,说清了自己的身份——市委办的科长——也许这样做有些不妥,但是我什么都不顾了。我请他打电话给廖主任。阿依也给这家医院的纪委书记打电话,她是我们拐弯抹角的一个亲戚。
然后,我们就在主任室见到了那个在小城医界大名鼎鼎的廖主任,她正在与几个医生商议着什么。
“廖主任……”阿依两眼含泪望着她说。
廖主任说:“放心吧,王院长和韦书记都打电话来了,韦书记昨晚还跟我说了你们的故事,哎,韦书记很了解你们的经历哦,她说她和你们是亲戚,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,我们聊你们聊了很久,小张你竟然是新疆人?真没想到。你们很不容易,我也是女人,明白养个女儿不容易,特别是你们,经历了那么多,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,你们看,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都推迟到明天下午了,我明天上午一定亲自给你们的女儿做。”
阿依直擦眼泪。我像押上了自己人生的全部筹码,既满怀希望又担心堕入深渊。
第二天上午八点多,依力被推到了儿科抢救室。助手医生先给她打了安定针剂,又做了局部麻醉,她很快睡着了,但是不到一分钟她又醒了,看到医生拿着针盒,大哭起来,喊:“不要打针,不要打针!”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。主任对我们说:“太奇怪了,做了麻醉还会醒,我从来没见过,但也不能注射第二次麻醉剂了,你们合力按住她,不能让她乱动。”那就是要在她清醒状态下做了?我和阿依十分惊愕,助理医生已经抓住她的双手,示意我抓住她的双脚,阿依按住她的腰。她似乎有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力气,我用尽力气,她依然能爆发出反抗的力量,主任说:“不行,你上床,用你的腿压住她的腿!”我就上床用自己的腿压住了她的两腿,双手还狠狠地扼住,依力还是拼命挣扎,但在我这个体重一百五十斤的父亲控制下,她已经动弹不得。我心痛地想,这就是给我们的女儿做手术吗?
主任伸手在依力的腰椎上摸索了一阵,找准了一个位于中间的位置,涂抹了消毒液,右手从针盒里取出一根足有十厘米长的穿刺针,阿依脸色都变白了,我的心像浸到了冰水里。当钢针被主任直直地刺进去的刹那,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喊声,我脑袋嗡地震了起来,心也在紧缩,在痛,似乎那根针刺进去的是我的腰椎,我痛得咬着牙忍受。也许是局麻的作用不大,依力的双腿一直在挣扎,要从我手里和腿下挣脱出来。我听见她大声喊妈妈,阿依答应着,眼里噙着泪,把头凑近她脑袋摩挲着,安慰她:“依力不哭,依力好样的,依力忍着点,就好了。”她又大声喊爸爸,我在她的脚边答应着,她又开始叫奶奶。
病房门口已经围聚了一群人,他们在议论:“哎,真可怜哪,这么小的妹儿,要受这种折磨。”
她肯定痛极了,她的痛只有我们做父母的知道,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穿心的痛苦,十分钟似漫漫长夜。更锥心的是第一次不理想,抽不出脑脊液,要第二次重来。我那一刻不只是对主任产生了怀疑还怨恨老天不照顾,心想这样失败的事怎么又摊在我们和依力身上。撕心裂肺的哭喊一直不停,第二个十分钟如漫长的十年,抽出来的竟然不是血,而是如水的液体,足足有三四毫升的样子。阿依和我哗哗泪流。依力还在撕心裂肺地哭喊,她的奋力挣扎,她变形一般的脸部,让我顿生一种欺负人的愧疚感。背着慈爱和养育责任的我们,还有扛着治病救人大旗的医生,就这样欺负了一个才三岁多的孩子。
穿刺做完后,她也哭累了,平静下来,趴在床上不动,我们心痛地哄着她,抚摸着她,像面对一件被失手打碎的宝贝,在经过高人小心的修补之后,我们心里充满了完好无损的期待。阿依紧紧把她搂在怀里,不住地吻她。
下午,医生公布结果时,我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晴天霹雳,脑脊液的蛋白数量达到了八百五十,是脑膜炎。我惊恐万分,像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,一切都将离我而去。凭着我们有限的那点知识都知道,脑膜炎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死亡,经过急性期的积极治疗后,一些患者仍留有不同程度的肢体运动障碍、智力障碍、失语、眼球麻痹、吞咽困难等后遗症。
一种浓稠的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我,我和阿依互相搀着进入病房,感觉脚上拖着万斤巨石,又轻飘如絮。阿依的眼眶已经陷进去了,我像来到了两个黑洞前。从牧区来的阿依脸色本来有些酱红,此刻却像一张白纸,把我的心也照得一片苍白。女儿啊,为了等到你来这个世间,爸爸妈妈饱尝了六年的冷嘲热讽,受尽了精神的折磨,妈妈还经受了肉体的病痛,我们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有了你,你出生在妈妈的故乡遥远的伊犁,你得到过外公外婆三个多月的悉心喂养,在我们的生命里,掌上明珠也无法跟你相比!可是,如今——你会不会困此而留下什么后遗症?甚至,你会不会因此离开我们?
我不敢想下去了。我深深地悲叹着,心已经被一块巨石榨出了最后的一滴血。
依力熟睡在床上,我和阿依目光呆滞地看看她,又互相对望一眼,然后把目光转向雪白的墙壁。那里,更加让我感到了一种空虚和冰凉。
人生遭逢的又一次不测让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我渐渐相信了命运,恍惚中想起了年初才去世的父亲,想起了那个骇人的说法。难道,这就是那个谶语在我们身上的灵验?
我开始埋怨在天国之上的父亲,你走得那么早,才五十八岁,还来不及退休,留给母亲和我们做儿子的一腔悲痛。本来,在天之灵要保佑自己在人世间的亲人,可是现在,那个谶语却灵验了,你明明知道你的孙女我们的女儿得之不易,却为什么让她得了这种可怕的病症?
那个下午,我的心头一直被那块巨石压着,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不是靠在依力的床头,就是在床头不约而同地靠在一起,我知道阿依是无力的,可我还是想借阿依的肩膀靠一靠。我看她也是这样的表情。依力安静地躺在床上睡着了。但是到了晚上七点多,她突然醒了,吵着要回家,我们怎么哄都不听,她的啼哭声震得同病房的患儿家属皱起了眉,隔壁病房的患儿家属也有了埋怨。未做穿刺术之前,阿依就担心麻醉对她这么小的孩子会留下什么后遗症,现在看到她的哭闹样,愁眉苦脸着。阿依一会儿给她测体温,一会儿给她喂水,一会儿抱她去拉尿,最后疲惫得站着都打瞌睡了。到了半夜三点,女儿说要喝牛奶,我冲了牛奶给她喝,她又要妈妈背背她,阿依疲倦地背着她在病房里踱步,我想接替阿依背一背,她不愿意,突然哭喊:“我要回家,我要回家!”哭得声嘶力竭,歇斯底里。阿依说:“可能是上午的腰穿术把她吓坏了。”她的哭喊声惊扰了一层楼,隔壁的许多患儿也被惊哭了,一些家属在走廊上埋怨和嘀咕。医生来了,护士来了,她依然哭着喊着,护士就拿出一支针管吓唬她说:“再哭就打针!”她惊恐地说:“不打针,不打针!”护士一走,她又哭起来,前后闹了近一个钟头,可能是累了,慢慢安静下来,最后睡着了。
我们凝视着她。她脸色蜡黄,两颊瘦削。两年多来我们省吃俭用,尽量供应我们认为一个幼儿必需的营养,奶粉拣名贵的买,三天两头是筒骨煲汤,从新疆回来后,她被我们养成了一个瓷娃娃。可不曾想,仅仅三天,她就瘦成了一只小麻雀。我真的在想,只要她转危为安,只要她健康活泼,就是要我去死,就是女儿今后一个人留在世上,我也心甘情愿。
“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我妈,”阿依还是不看我,泪水却已滴在依力的病床上,“给他们知道,我怎么交代?”
她的哭声出来了,低低的呜咽。
是啊,是告诉依力外公外婆的时候了,就算不是恐惧和绝望,也是寻找安慰和依靠。
我一直担心阿依打电话会哭,但是她完全调整好了心情。虽然相隔着五百多公里,在东莞的老人听了阿依低沉而又稍显迟疑的讲述,我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焦急的表情,阿依母亲一会儿问我们需要不需要钱,一会儿说他们马上过来。我赶紧朝阿依摆摆手,阿依稍稍恢复了镇静:
“你们不用过来,只是做了一个小手术,过些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“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,平时该做的体检和防疫都做了没有?一定要找最好的医生,绝不能留下后遗症!”
然而,在给依力外公外婆打电话后不到两个小时,她的体温就出现了反复,有时36度多,有时达到39度。刚刚放下的心又被吊起来,压力又像一座山压在心上。当晚又开始输降温药水,我们一夜没睡,第二天她的体温依然高低不定。
上午,单位来电话了,说领导在自治区发言的材料没有通过,稿子返工了两次,书记马上要看材料了,让我回去修改。阿依看着我,我满腔悲愤,阿依且说:“你还是回去看看吧,有什么事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那个中午和下午,我带着愤怒的情绪改完了稿子,将数据补充和校对的工作留给他们,一言不发跑回医院。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睡过完整的觉了。晚上,同病房的两个患儿都是他们的母亲陪护,房内摆满了躺椅,我要摆一张椅子都已无处立足,只好将椅子摆在了走廊外。阿依在依力住院前就规规矩矩地写了请假条,领导批准后她还复印了自存,见我在病房里为了工作骂骂咧咧,怕我丢了这份既像牛马一般又似乎前途无限的职业,劝我回家去睡上一觉。
“你回去休息一晚吧,这样也可以应付办公室的工作,这里我扛得住。”
“我不走,我就是放不下心,我熬夜惯了,你先睡,下半夜我再睡。”
医生的规定很特殊,晚上十点输一次药水,午夜一点还要输一次。阿依侧身躺在病床上抱着依力,半寐半醒,两次换药水她都醒来,两点之后我也睡不着了,我们就靠在床上护着依力假寐。
第二天,主任说:“我们讨论了,需要用罗氏芬菌必治来治疗,这是一种进口药,医院暂时短缺,干脆你们自己去地区或者南宁购买吧,这样快一点。”
我不能怪儿科主任不帮我想办法,她已经很尽责了,我亲眼看见她一个上午都没有闲过,围着她的全是婴幼儿的哭声和他们母亲焦虑忧愁的目光。而且她在一次查房时,大概是看到了我一脸的愁容,趁着旁边的患儿家属出去了,悄悄安慰我说:“我感觉到了,你很爱你女儿,我看你女儿的次数都比他们多,我会尽力的,你听我讲,你女儿肯定会好的。”
我和阿依望着她,不停地点头。突然我很想哭。
下午一直下着大雨,我心急火燎冒雨乘车去地区第一医院询问,没有,再去地区骨科医院问,也没有,心里顿时有了哭的感觉。医生建议我去南宁,南宁,乘车来回要六七个钟头,去南宁必定是当天傍晚才到,买好药再赶回小城肯定是明天下午了。
雨一直在下着,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,一种像雨又像梦的忧愁完全罩住了我。
就在我要往车站赶时,大弟打来了电话,他有一个熟人当晚将从南宁回来。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一下子就托人狂购了十支,这种药分国产和进口,我们买的是进口药,比国产贵三分之一,每支九十块钱。我们哪里还敢计较价钱呢,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完了,又向弟弟借了一笔钱。
当护士开始给依力输这种药液的时候,我默默地靠在病床上,看着微黄的药水一滴一滴地通过洁白的管道注入依力的手臂,回想起了自己此前走过的路,既艰辛也幸运,让我越来越相信天意。天在我几乎慌不择路的时候,借身一个人帮助了我们,我看见它的善心布满了看不见的空间,它让渺小无助的我对它感激涕零。
在用过罗氏芬菌必治三天后,依力的体温恢复正常了。当我看到她睁开了依然清澈的大眼睛,瘦削的脸蛋也浮现了浅浅的笑容,我和阿依都流泪了。那一刻,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感觉,这世上,除了她,再也没有一个亲人!
依力又睡着了,我和阿依仿佛大病初愈,头靠着病床架斜躺在依力两边,微微闭着眼睛。我又开始愧疚地想,还有阿依,这世上,还有她才是我的亲人。不,我所有的亲人,现在都慢慢地回来了,他们都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已经是晚上十一点,阿依让我回家休息,她说:“我在这里就够了,你休息好,明天换一下我。”带着疲倦和宽心,我回到了家里。但是夜里三点多,手机响了,阿依焦急地说:“依力醒了,哭着要爸爸,歇斯底里的,我怎么劝都不行。病房里的两个孩子都被吵哭了,他们的母亲抱出去躲了。”
我赶紧起床,到楼下发动车子,开了车灯,发现灯光比平时夜里要雪亮,我猜想应该是夜很黑。许多条街道空无一人,只有西门口和东门口的夜宵摊还有几帮聚在一起的青年人喝酒喊令——他们如此开心——我想。我将车子开到了七十迈,摩托车像飞机一般轰鸣着,我赶到儿科住院部,才进走廊就听到了熟悉的哭声,并一声接一声地喊着:“我要爸爸——我要爸爸!”我快步踏进病房,依力正在阿依怀里挣扎,我喊了一声,她扭头见了我,带着哭腔扑过来,我把她揽在怀里,给她擦着眼泪,她抽噎着,一直到累了才慢慢睡去。因为我抱着她刚弯腰想放在床上,她的背部还没碰到床就哭起来,像猴子一般双手吊着我的脖子不放,我只好继续抱着她。她又睡着了,但肩膀一抖一抖,她在梦中抽泣。我坐在病床上,阿依凑过来扶着她,默默垂泪。
同病房的两位母亲已经抱着他们的孩子回来,对依力刚才的吵闹不再计较,一个对阿依说:“真佩服你哋,我哋的女儿病了,老公来冇够两次,家公家婆一次都冇来过。都说我哋南方重男轻女,这位做爸爸的亦系南方人吧,你咁爱女儿,难得啊!”
我望了望她们,再看看阿依,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。我想起了父亲母亲。当初,依力回到南方后,不知道是父亲对我多年未得子女的欣慰,还是依力长得可爱,他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父亲是矛盾的,他一直希望有孙子,当他看着左邻右舍逗弄孙子时总不免羡慕。有一年春节在老家地坪上,他牵着依力的两手表情陶醉地教她走路,旁边来了几个逗弄孙子的叔伯,他们拿眼看着父亲,大声对着自己的孙子喊:“走呀,快走,难道你站着尿尿的还走不过那边蹲着尿尿的吗?”父亲假装看不到也听不到。
父亲逝去后,我开始从身体和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他,我认为,父亲在患上绝症之前,已经因为我们迟迟没有孩子而患了抑郁症,当这种抑郁成为常态,也就积累成了他的身心疾病。我敢说,他的后期绝症与前期的抑郁症有紧密关系。从心理健康角度而言,父亲当时的状态,诚如母亲传递给我的那句话“肾都忧凹了”,父亲就是在抑郁状态中使身体失去了健康对疾病的平衡,最终患上了绝症,走上了不归路。反思父亲疾病的起源,包括前期的抑郁症和后期的绝症,归根结底缘于我作为他的长子,也是家里唯一的国家干部,多年没有生育,后来虽然有了依力,但没有给他这个家添上男丁,无法完成延续子孙的责任,这对深受宗族礼教思想影响的父亲而言,当然是致命的病因。
那天依力出院时,我母亲很想借机亲近她,说帮她洗,她不愿,哭哭啼啼说要爸爸洗。母亲讪讪地笑着。阿依在一边笑着说:“肯定是住院这些天她跟我们太亲密了,她都不认奶奶了。”我给她洗的时候,她果然破涕为笑。
两个月后我们忐忑不安地带依力去复检,就像等候自己命运的宣判。当儿科主任高兴地宣布她已经完全康复时,我紧紧地搂住她,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浮上心头。阿依凑过脸流着泪亲她,声音卜卜响,边亲边哽咽着说:“你这个让人揪心的——丑丑啊,丑丑啊!”
生存的环境我们是无法改变的,在这个偏远的小城,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“有人就有物”“多子多福无子无福”的观念不时在耳边炸响。回想那些意想不到的逝去,我只有深深的叹息,而对于今天饱经沧桑的获得,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,并且对这个世界深深感恩。
后来我们一家三口有过几次从广西回到新疆的漫长旅途,三天三夜的旅程,我们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依力。几乎每一次,车厢上总有几位非常喜欢她的大姐大嫂拿出她们小孩也在吃的瓜果、干果给她,依力早就得到我们不吃陌生人食物的教导,开始是摆手,随着旅途的熟稔,终于盛情难却,况且是在列车上,我们允许她接受,但是面对女儿转手递过来的零食,我们的底线是夫妻坚决不吃不碰,哪怕女儿中了迷药,那一刻也有她爸爸妈妈守在她身边。
有一次在老马场,晚饭后伊犁台正在播放一男一女两位当地歌手演唱《牡丹汗》,依力喊:“咦,这是爸爸经常给我唱的歌!”我诡秘地笑。她问:“牡丹汗是什么意思,是牡单丫吗?”阿依看着她说:“是个名字。”我趁机指着电视说:“对,那女的就是那男的牡丹汗,你和妈妈就是爸爸的牡丹汗。”她疑惑地看着我,又看看电视里的歌手,他们正在深情而忧郁地唱:
你是我生命的力量
啊,亲爱的姑娘啊牡丹汗
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
啊,我的姑娘
亲爱的牡丹汗
月亮躲在云彩的后面
啊,亲爱的姑娘啊牡丹汗
晨风莫吹断我的思念
啊,我的姑娘亲爱的牡丹汗
……
一首维吾尔族情歌,我曾在哄依力睡觉时在她身边唱,在她熟睡后依然轻声地唱,我轻抚着她的脸蛋和肩背,歌曲一直在我的心底悄悄地唱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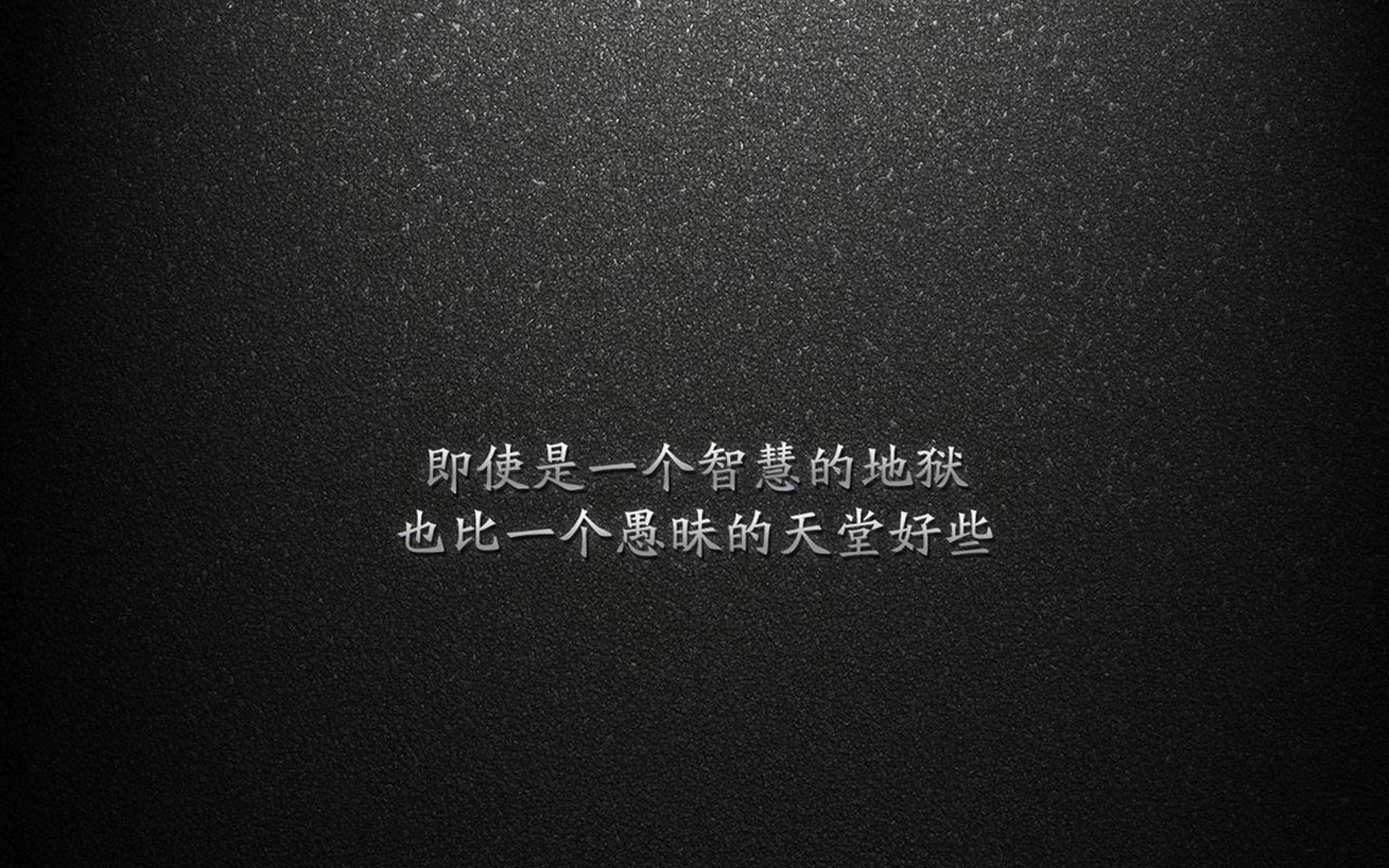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